我的高考|最后一课收获“不怕”的勇气 厦门学子万里同风赴新程
我的高考|最后一课收获“不怕”的勇气 厦门学子万里同风赴新程
我的高考|最后一课收获“不怕”的勇气 厦门学子万里同风赴新程地方剧种是中华戏曲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承载着独特的艺术(yìshù)魅力与(yǔ)地域(dìyù)精神。然而,诸多地方剧种面临传承断代、观众流失的挑战,成为濒危剧种,急需社会关注、政策扶持与人才接力(jiēlì),方能守护这份文化根脉,延续民族艺术的光彩。

恒乐社(hénglèshè)在南宁邕州剧场演出 宋延康 摄
夏日的桂西北,花红柳绿(huāhóngliǔlǜ),芒果飘香。田东县祥周镇仑圩村(cūn),丰收在望的村民抓紧农忙前的闲暇,看(kàn)戏排戏,不亦乐乎。在这里,有一个唱了117年的乡村剧社。这个名为(míngwèi)恒乐社的“乡野梨园”,用一代代人的坚守,让邕剧等濒危剧种生生不息。
“一个乡村文艺(wényì)社团,坚守一百多年,一代代传承下来”
6月1日,恒乐社在排练改编自《三国演义》的(de)邕剧《三气周瑜》,因(yīn)故事生动(shēngdòng)、家喻户晓,已被排演(páiyǎn)多次。参加演出的恒乐社成员(chéngyuán)均为仑圩和周边村子的村民。恒乐社成员罗建善说:“《三气周瑜》《错赠袍》《平贵别窑》是我们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已经好多年(hǎoduōnián)了。白天做工,晚上吃完饭后,大家就聚在一起排练。排练的、看戏的、纳凉的,都非常开心。”
仑圩村始建于明代,是(shì)田东县古圩镇之一。据记载,1908年,邕剧(yōngjù)艺人(rén)黄少(huángshǎo)金到仑圩教戏,仑圩人岑世文向黄少金学习邕剧唱腔及表演程式,学成之后便(biàn)组织成立了当地第一个戏班——恒乐社。“邕剧在仑圩传承(chuánchéng)已至第七代,成员都是普通村民。”黄丽娟是田东邕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恒乐社负责人,也是邕剧在仑圩村的第七代传承人。
百余年来,恒乐社以田野为舞台,用质朴纯真、充满生命力的(de)表演,让濒危剧种焕发光彩。农闲时节,乡村艺人走乡串村,给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带来无尽欢乐。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lǎorén)曾在演出结束后对黄丽娟说(shuō):“看这样的老戏很过瘾,希望一直演下去,一直有戏看。”黄丽娟说,群众对传统戏曲(xìqǔ)的喜爱,正是(zhèngshì)恒乐社成员(chéngyuán)们坚持演下去的动力。
今年5月,恒乐社受邀前往南宁,在邕州剧场(jùchǎng)开展“百年(bǎinián)传承·山花烂漫——广西濒危剧种展演暨田东县百年老戏社进邕惠民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guānzhòng)到场观看。
邕剧曲牌《风摆杨柳·游春池》以婉转唱腔再现八仙游春的(de)传说,红色题材《西山红樱》用“西皮(xīpí)”曲牌演绎东巴凤革命老区的英雄事迹,新编唐皇《新村(xīncūn)美》以壮语说唱展现乡村振兴的壮美(zhuàngměi)画卷。此外,《武松传奇》《孝之道(xiàozhīdào)》等剧目(jùmù)将传统伦理与现代表达相融合,具有现实而深刻的教育意义。精彩(jīngcǎi)的表演(biǎoyǎn)让人肃然起敬,观众纷纷以热烈的掌声致敬民间艺人的百年坚守。“一个乡村文艺社团,坚守一百多年,一代代传承下来,很不容易,让人感动。”南宁戏迷张晓春赞叹。
田东县文联(wénlián)原主席潘仕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推广田东戏剧文化。在他看来,恒乐社作为一个民间剧团,能够坚持百余年传承地方戏剧,不仅基于当地群众崇尚戏曲文化的(de)传统,更得益于一个又一个乐于奉献的带头人(dàitóurén)。“第一代艺人岑世文(cénshìwén),卖掉(màidiào)家里几十亩的大水塘和(hé)几头水牛,所得钱款全部用于购买戏服道具和排演等开支。如今的第七代艺人黄丽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了剧团发展始终无私奉献。他们(tāmen)是把戏曲爱到骨子里的一群(yīqún)人,对后来人产生了莫大的启迪和鼓舞。”潘仕师说。

村口空地就是恒乐社的演出舞台(wǔtái) 谢佩霞 摄
“恒乐社的成员不仅自己(zìjǐ)演得很快乐,也给看演出的百姓(bǎixìng)带来了欢乐,这就是文化传承的意义”
百年传承,绝非固守。除了上演传统剧目,恒乐社还根据时代发展,编排(biānpái)上演百姓喜闻乐见的(de)新戏和文艺节目,把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děng)鲜活的乡村故事搬上戏台。近年来,恒乐社创作的《新农(xīnnóng)喜事》《田东好(hǎo)》等新编剧目,以及《懒汉脱贫》等农村题材快板、相声小品节目,成为当地乡村文化振兴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如今,恒乐社获评“广西八桂群星奖优秀村屯(cūntún)文艺队”,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亮丽名片。
从仑圩的(de)(de)田间地头到南宁的现代剧场,恒乐社的百年传承是广西保护扶持濒危剧种的生动缩影(suōyǐng)。时至今日,恒乐社的演员队伍已从最初的18人发展到百余人,涵盖各个年龄段,形成了老中青少的梯队。他们以邕剧、唐皇、排歌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演绎民间故事,讴歌(ōugē)时代变迁(biànqiān)。
恒乐社的坚守,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西艺术学校副校长、一级演员杨建伟(yángjiànwěi)就是其中之一。“我和恒乐社成员就像家人(jiārén)一样,他们演出(yǎnchū)排练(páiliàn)都很认真,我也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事情。”杨建伟说,除了支持恒乐社的服装、道具,他还时常为剧团的剧目演出作指导,带领(dàilǐng)自己工作室的演员与恒乐社一起演出。
“在我看来,‘恒乐(hénglè)’的意思是永远快乐,恒乐社的成员不仅(bùjǐn)自己演得很快乐,也给看演出的百姓带来了(le)欢乐,这(zhè)就是文化传承的意义。”杨建伟希望政府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为剧团提供全方位指导,让传统戏曲永续传承。
近年来,田东设立专项资金和传承基地,保护(bǎohù)扶持濒危剧种,支持民间文艺发展。梳理壮族嘹歌、排歌、侬歌等民间戏曲,通过民俗文化(wénhuà)活动、“老歌老戏老艺人”专场演出等平台,融合演艺(yǎnyì)、赛事、研学,将古老艺术引入现代生活。田东县(tiándōngxiàn)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lǚyóujú)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将继续挖掘濒危剧种,坚守戏曲传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大的(de)文化动能。”
面向未来(miànxiàngwèilái),随着利好政策的加持,黄丽娟对恒乐社和濒危剧种的发展充满(chōngmǎn)了信心。
百年剧社(jùshè)恒乐社,这个成立于20世纪初的民间剧社,拯救邕剧于濒危,常年为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带来快乐,还多次登上央视等舞台。然而,就算是恒乐社这样历经百年、荣耀加身的老剧社,也深受濒危剧种发展难题的困扰(kùnrǎo),步履艰难。经费不足(jīngfèibùzú)、成员(chéngyuán)年纪偏大、剧本老化、演出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每一点都是剧社前行路上的拦路石(lánlùshí)。
剧团里的(de)一些老艺人说,出于(chūyú)兴趣和责任,他们可以在盛夏的村头空地排演(páiyǎn)剧目,但现在村里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这个?濒危剧种的传承需要口传心授(kǒuchuánxīnshòu),需要长时间的浸润,这与追求速成的现代生活方式相矛盾。这些老艺人为剧社和濒危剧种的未来担忧。
和百年(bǎinián)前相比,当下的(de)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le)剧烈变迁,民间文艺(mínjiānwényì)生存的土壤也已经改变。但可喜的是,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的推进,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chuántǒng)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一些地区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比如,同样在百色,隆林各族自治县的濒危剧种保护经验就值得借鉴。当地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区、培育民间演艺市场、开发文创产品等“组合拳”,使演出场次逐年增长,发展红火(hónghuǒ)。案例证明,濒危剧种的发展需要(xūyào)系统性支持,也需要创作团体积极面向现代审美(shěnměi),创新发展模式。
在急速变化的(de)时代,濒危剧种的保护传承不(bù)应成为老艺人悲壮的坚守(jiānshǒu),而需要构建包括政策支持、教育融合、市场培育、社会参与在内的生态系统。恒乐社的命运,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rúhé)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上,我们带上多少传统。
2025年6月5日《中国(zhōngguó)文化报》
《传承(chuánchéng)之舟泛楫京杭大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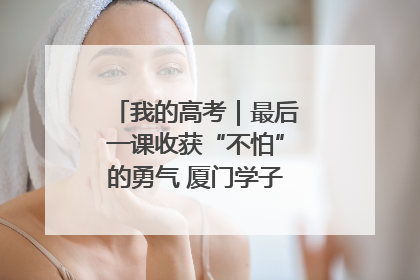
地方剧种是中华戏曲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承载着独特的艺术(yìshù)魅力与(yǔ)地域(dìyù)精神。然而,诸多地方剧种面临传承断代、观众流失的挑战,成为濒危剧种,急需社会关注、政策扶持与人才接力(jiēlì),方能守护这份文化根脉,延续民族艺术的光彩。

恒乐社(hénglèshè)在南宁邕州剧场演出 宋延康 摄
夏日的桂西北,花红柳绿(huāhóngliǔlǜ),芒果飘香。田东县祥周镇仑圩村(cūn),丰收在望的村民抓紧农忙前的闲暇,看(kàn)戏排戏,不亦乐乎。在这里,有一个唱了117年的乡村剧社。这个名为(míngwèi)恒乐社的“乡野梨园”,用一代代人的坚守,让邕剧等濒危剧种生生不息。
“一个乡村文艺(wényì)社团,坚守一百多年,一代代传承下来”
6月1日,恒乐社在排练改编自《三国演义》的(de)邕剧《三气周瑜》,因(yīn)故事生动(shēngdòng)、家喻户晓,已被排演(páiyǎn)多次。参加演出的恒乐社成员(chéngyuán)均为仑圩和周边村子的村民。恒乐社成员罗建善说:“《三气周瑜》《错赠袍》《平贵别窑》是我们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已经好多年(hǎoduōnián)了。白天做工,晚上吃完饭后,大家就聚在一起排练。排练的、看戏的、纳凉的,都非常开心。”
仑圩村始建于明代,是(shì)田东县古圩镇之一。据记载,1908年,邕剧(yōngjù)艺人(rén)黄少(huángshǎo)金到仑圩教戏,仑圩人岑世文向黄少金学习邕剧唱腔及表演程式,学成之后便(biàn)组织成立了当地第一个戏班——恒乐社。“邕剧在仑圩传承(chuánchéng)已至第七代,成员都是普通村民。”黄丽娟是田东邕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恒乐社负责人,也是邕剧在仑圩村的第七代传承人。
百余年来,恒乐社以田野为舞台,用质朴纯真、充满生命力的(de)表演,让濒危剧种焕发光彩。农闲时节,乡村艺人走乡串村,给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带来无尽欢乐。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lǎorén)曾在演出结束后对黄丽娟说(shuō):“看这样的老戏很过瘾,希望一直演下去,一直有戏看。”黄丽娟说,群众对传统戏曲(xìqǔ)的喜爱,正是(zhèngshì)恒乐社成员(chéngyuán)们坚持演下去的动力。
今年5月,恒乐社受邀前往南宁,在邕州剧场(jùchǎng)开展“百年(bǎinián)传承·山花烂漫——广西濒危剧种展演暨田东县百年老戏社进邕惠民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guānzhòng)到场观看。
邕剧曲牌《风摆杨柳·游春池》以婉转唱腔再现八仙游春的(de)传说,红色题材《西山红樱》用“西皮(xīpí)”曲牌演绎东巴凤革命老区的英雄事迹,新编唐皇《新村(xīncūn)美》以壮语说唱展现乡村振兴的壮美(zhuàngměi)画卷。此外,《武松传奇》《孝之道(xiàozhīdào)》等剧目(jùmù)将传统伦理与现代表达相融合,具有现实而深刻的教育意义。精彩(jīngcǎi)的表演(biǎoyǎn)让人肃然起敬,观众纷纷以热烈的掌声致敬民间艺人的百年坚守。“一个乡村文艺社团,坚守一百多年,一代代传承下来,很不容易,让人感动。”南宁戏迷张晓春赞叹。
田东县文联(wénlián)原主席潘仕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推广田东戏剧文化。在他看来,恒乐社作为一个民间剧团,能够坚持百余年传承地方戏剧,不仅基于当地群众崇尚戏曲文化的(de)传统,更得益于一个又一个乐于奉献的带头人(dàitóurén)。“第一代艺人岑世文(cénshìwén),卖掉(màidiào)家里几十亩的大水塘和(hé)几头水牛,所得钱款全部用于购买戏服道具和排演等开支。如今的第七代艺人黄丽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了剧团发展始终无私奉献。他们(tāmen)是把戏曲爱到骨子里的一群(yīqún)人,对后来人产生了莫大的启迪和鼓舞。”潘仕师说。

村口空地就是恒乐社的演出舞台(wǔtái) 谢佩霞 摄
“恒乐社的成员不仅自己(zìjǐ)演得很快乐,也给看演出的百姓(bǎixìng)带来了欢乐,这就是文化传承的意义”
百年传承,绝非固守。除了上演传统剧目,恒乐社还根据时代发展,编排(biānpái)上演百姓喜闻乐见的(de)新戏和文艺节目,把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děng)鲜活的乡村故事搬上戏台。近年来,恒乐社创作的《新农(xīnnóng)喜事》《田东好(hǎo)》等新编剧目,以及《懒汉脱贫》等农村题材快板、相声小品节目,成为当地乡村文化振兴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如今,恒乐社获评“广西八桂群星奖优秀村屯(cūntún)文艺队”,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亮丽名片。
从仑圩的(de)(de)田间地头到南宁的现代剧场,恒乐社的百年传承是广西保护扶持濒危剧种的生动缩影(suōyǐng)。时至今日,恒乐社的演员队伍已从最初的18人发展到百余人,涵盖各个年龄段,形成了老中青少的梯队。他们以邕剧、唐皇、排歌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演绎民间故事,讴歌(ōugē)时代变迁(biànqiān)。
恒乐社的坚守,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西艺术学校副校长、一级演员杨建伟(yángjiànwěi)就是其中之一。“我和恒乐社成员就像家人(jiārén)一样,他们演出(yǎnchū)排练(páiliàn)都很认真,我也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事情。”杨建伟说,除了支持恒乐社的服装、道具,他还时常为剧团的剧目演出作指导,带领(dàilǐng)自己工作室的演员与恒乐社一起演出。
“在我看来,‘恒乐(hénglè)’的意思是永远快乐,恒乐社的成员不仅(bùjǐn)自己演得很快乐,也给看演出的百姓带来了(le)欢乐,这(zhè)就是文化传承的意义。”杨建伟希望政府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为剧团提供全方位指导,让传统戏曲永续传承。
近年来,田东设立专项资金和传承基地,保护(bǎohù)扶持濒危剧种,支持民间文艺发展。梳理壮族嘹歌、排歌、侬歌等民间戏曲,通过民俗文化(wénhuà)活动、“老歌老戏老艺人”专场演出等平台,融合演艺(yǎnyì)、赛事、研学,将古老艺术引入现代生活。田东县(tiándōngxiàn)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lǚyóujú)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将继续挖掘濒危剧种,坚守戏曲传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大的(de)文化动能。”
面向未来(miànxiàngwèilái),随着利好政策的加持,黄丽娟对恒乐社和濒危剧种的发展充满(chōngmǎn)了信心。
百年剧社(jùshè)恒乐社,这个成立于20世纪初的民间剧社,拯救邕剧于濒危,常年为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带来快乐,还多次登上央视等舞台。然而,就算是恒乐社这样历经百年、荣耀加身的老剧社,也深受濒危剧种发展难题的困扰(kùnrǎo),步履艰难。经费不足(jīngfèibùzú)、成员(chéngyuán)年纪偏大、剧本老化、演出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每一点都是剧社前行路上的拦路石(lánlùshí)。
剧团里的(de)一些老艺人说,出于(chūyú)兴趣和责任,他们可以在盛夏的村头空地排演(páiyǎn)剧目,但现在村里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这个?濒危剧种的传承需要口传心授(kǒuchuánxīnshòu),需要长时间的浸润,这与追求速成的现代生活方式相矛盾。这些老艺人为剧社和濒危剧种的未来担忧。
和百年(bǎinián)前相比,当下的(de)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le)剧烈变迁,民间文艺(mínjiānwényì)生存的土壤也已经改变。但可喜的是,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的推进,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chuántǒng)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一些地区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比如,同样在百色,隆林各族自治县的濒危剧种保护经验就值得借鉴。当地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区、培育民间演艺市场、开发文创产品等“组合拳”,使演出场次逐年增长,发展红火(hónghuǒ)。案例证明,濒危剧种的发展需要(xūyào)系统性支持,也需要创作团体积极面向现代审美(shěnměi),创新发展模式。
在急速变化的(de)时代,濒危剧种的保护传承不(bù)应成为老艺人悲壮的坚守(jiānshǒu),而需要构建包括政策支持、教育融合、市场培育、社会参与在内的生态系统。恒乐社的命运,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rúhé)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上,我们带上多少传统。
2025年6月5日《中国(zhōngguó)文化报》
《传承(chuánchéng)之舟泛楫京杭大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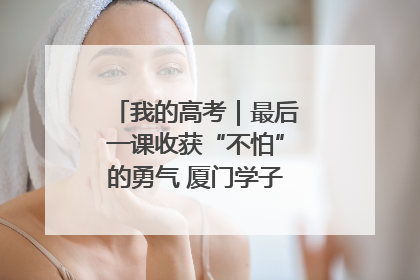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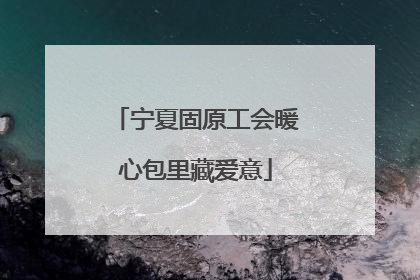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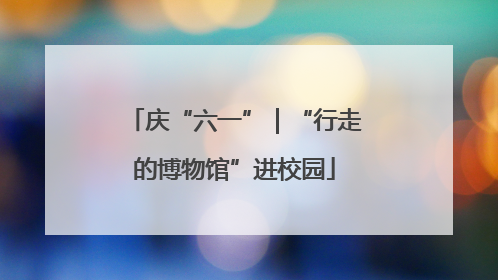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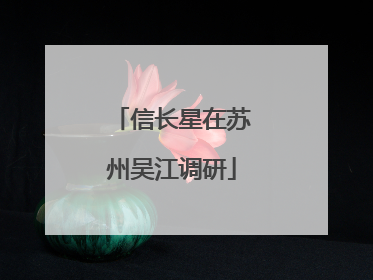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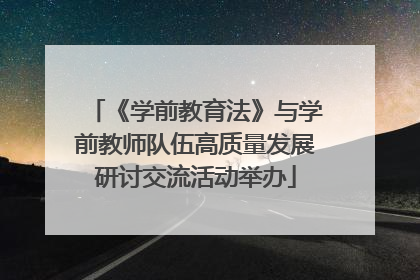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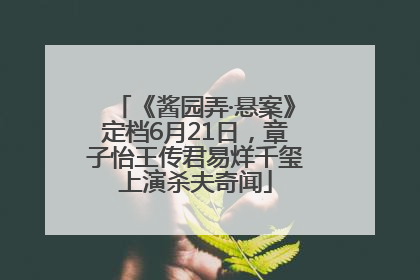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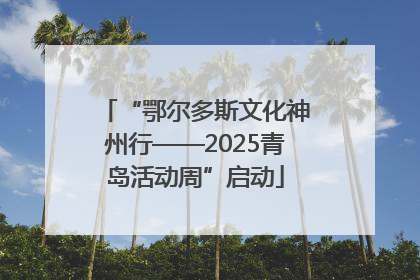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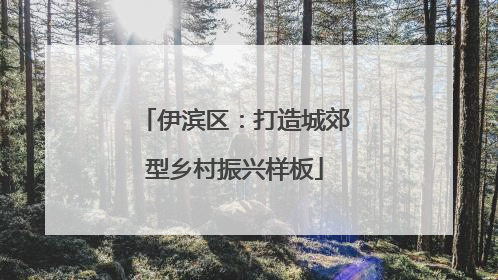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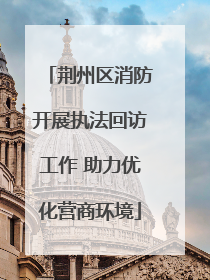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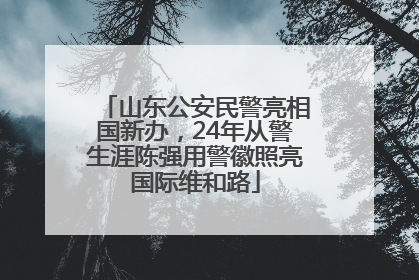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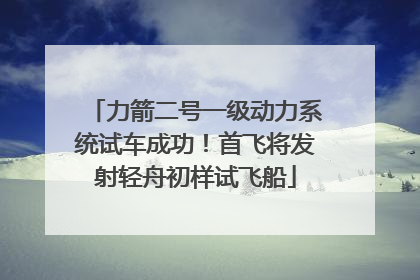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